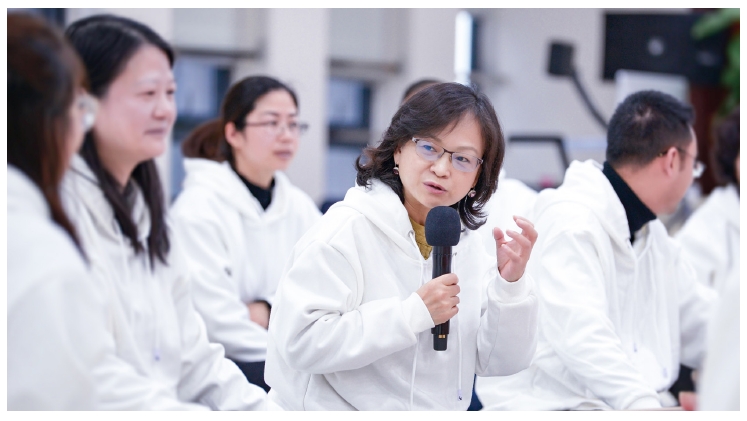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主体通过竞争,让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在招投标项目中,投标人通过公平竞争以其可接受的合理价格获得相应的项目,招标人也借此获得性价比最高的产品或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在我国境内进行以下三种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这三种工程建设项目分别是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但实践中规避招标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情况的背后往往存在有关部门的失职渎职,甚至利益输送;相应招标项目也往往存在质量隐患,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难以保障。先施工后“补标”、将公开招标改为邀请招标、将依法必招项目改为其他采购方式等规避招标行为,不仅违反了《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还可能涉嫌串通投标罪、滥用职权罪等。
事后“补标”行为要区分情况认定
事后“补标”(事后补办了招标投标手续)行为在建设工程招标采购活动中比较常见,情况复杂,是否构成犯罪不可一概而论。根据投标人对招标活动的参与程度、对招投标程序走向的实质影响力,大体可将事后“补标”行为分为“共谋实施型”和“被动参与型”。前者是投标人与招标人共同策划,由内定投标人采取先施工后补标方式,规避正常招标程序;后者是招标人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正常招投标程序采购,确定投标人先行施工,而后为完善程序补充招标,此过程完全由招标人一方主导,投标人只是被动参与或配合。
第一,“共谋实施型”先施工后补标行为,原则上构成串通投标罪。
对应当招标的项目,招标人与投标人共谋,先施工后补标,以规避正常招投标程序的,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且具有刑事可罚性,构成串通投标罪。例如,某国有企业A以某项目施工技术要求高、工期紧张为由,内定某企业B先行施工,待施工接近尾声时为完善手续才后补招标流程,由B组织其关联企业参与投标,B顺利中标。事后查明,系A、B两企业相关负责人员共谋,采取先施工后“补标”,以排斥其他企业参与的方式,确保B企业顺利获得建设项目。此种情况是属于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损害国家、集体、公民合法权益”不要求必须有可量化的损失。因为,故意规避正常招标程序的行为本身就已经侵害了国家或有关法人、组织通过招投标程序选择价低质优的产品或服务的机会。这种机会成本的丧失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权益损害。除此之外,这种先内定后“补标”的行为,必然会对项目建设或产品采购造成实际影响,如项目能否通过验收、质量优劣与否、价格高低与否。这些实际影响都属于可以通过调查取证予以查明的情况。至于A企业负责人是否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以及如何处罚问题,则属于另一层面问题。
第二,“被动参与型”先施工后“补标”行为,投标人不构成串通投标罪,招标人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某镇政府负责人张某为迎接上级检查,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道路绿化任务(属于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于是找到从事绿化工程的C公司负责人李某,商定由李某先行承接该绿化工程并马上开工,随后补充完善招投标手续。在施工接近尾声时,镇政府组织该绿化项目的招投标,在张某的支持下,李某组织包括C公司在内的5家企业投标,C公司中标。
本案例中,如果单看李某事后组织有关企业投标的事实,其“外观”上符合投标人之间串通投标的情形,但在该项目的承接、施工和招投标手续完善等方面,完全由镇政府主导,李某系被动参与。即李某组织企业投标的行为虽然形式上符合串通投标罪的犯罪构成,但实质上并未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况且,这种情况下,很难期待李某有实施其他适法行为的可能。因此,应当否定张某、李某构成串通投标罪。但作为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张某实施了违背《招标投标法》的滥用职权行为,如果该行为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则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将公开招标改为邀请招标
对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将公开招标改为邀请招标的行为如何定性,一方面要分析当事人的行为本质,判断其是否符合串通投标罪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要注意当事人的身份,全面判断行为性质。
第一,工程建设领域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将公开招标改为邀请招标,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的,构成串通投标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的规定,除了两种特殊情况外,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均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现实中,有的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将本该公开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再采取邀请招标的方式。虽然都是招标,但是邀请招标与公开招标相比,投标参与人范围窄、竞争不充分。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更改招标方式,本质上是为了控制投标参与人的范围,排斥其他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参与竞争,以使有关投标人中标。这种情形违反了《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属于“招标人与投标人为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而采取的其他串通行为”的情形;如果达到了串通投标罪的追诉标准,则招标人与投标人均构成串通投标罪。
第二,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活动中采购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的情形。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四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采购人即为招标人,供应商则为投标人。因此,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将公开招标改为邀请招标,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且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则构成串通投标罪。需要说明的是,在政府采购中,与供应商/投标人串通的,往往并非作为采购人/招标人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而是其中的采购/招标人员。这些采购/招标人员能否成为串通投标罪的主体?笔者以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中的招标人、投标人是指招投标活动的参与人,而并非仅限于《招标投标法》意义上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参与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活动的采购/招标人员可以构成串通投标罪。同时,采购/招标人员如果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还涉嫌滥用职权犯罪。具体来说,如果采购/招标人员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涉嫌滥用职权罪;如果是国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则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此时采购/招标人员一人犯数罪,在罪数处断上,应在串通投标罪与滥用职权犯罪之间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第三,在政府采购货物、服务的招投标活动中串通投标的情形。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对政府采购货物、服务的招标投标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对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的招投标规定与《招标投标法》之间是“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当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对政府采购货物、服务的招投标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则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不管是《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关于政府采购货物、服务的招投标的规定,还是《招标投标法》及其条例的规定,都是规范招投标行为的。如果在政府采购货物、服务的招投标活动中采购/招标人员与供应商/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则供应商/投标人涉嫌串通投标罪,采购/招标人员则同时涉嫌串通投标罪和滥用职权犯罪,处罚原则也是择一重罪定罪处罚。例如,江苏省某市信息中心原副主任杜某作为国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负责“南京市城市智能门户运维托管”等多个项目招投标工作期间,与相关企业负责人串通投标,并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同时构成串通投标罪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因其所犯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较重,最终以该罪定罪处罚。
应当招标而采取询价方式的处理
某地政府财政预算8亿元,分两次以询价方式采购新城建设所需苗木。甲园林公司得知消息后,与其他5家园林公司共谋在该项目中串通投标,由甲园林公司统一制作《投标报价书》、统一支付保证金、统一组织参与询价竞标。在首次询价采购的现场询价环节,包括甲园林公司在内的6家园林公司投标文书几乎相同,被评审专家作否决投标处理。之后,该苗木项目重新启动,甲园林公司完善了相关资料,最终在两次询价采购中均以最低报价成交,取得《中标通知书》,成为该苗木项目供应商。本案例中,行为人违法以询价方式采购本应招标的苗木项目。在采购过程中又出现“询价竞标”“投标报价书”“中标通知书”“废标”等字眼,模糊招标采购与询价采购的界限。对此,应当区分情况处理。如果采购过程表面上看似是询价,但实际上按照招标流程采购,且该项目本就属于应当招标的情形,那么行为人对“投标报价”进行串通的,应当构成串通投标罪。如果将应当招标的项目违法采取询价的方法采购,且符合询价采购程序的,行为人在询价中串通报价的,属于对“询价”的串通,而非对“投标报价”的串通;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存在招投标的形式,也不存在招投标的实质,因而不存在“串通投标”的行为,故难以认定行为人构成串通投标罪。
投标人之间对“报价”外事项的串通
《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了串通投标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另一种是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在某案件中,甲、乙、丙、丁四家单位在投标某地灯光秀设备采购项目中,未就投标报价串通,而是对招标项目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参数进行串通,并据此中标。有观点认为,“投标报价”中的“价”既有“价格”之意,也有“价值”之意,故可对串通投标报价中的“投标报价”扩大解释为“投标人为响应招标,通过投标文件等所报出或出示的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实质性事项或条件所具有的价值或作用。”
笔者认为,投标人之间对“报价”外事项的串通不构成串通投标罪。众所周知,文义解释是最基础的法律解释方法,法条“可能的语义”就是法律解释的界限。超出了“可能的语义”,这种解释便不是扩大解释,而是类推解释。《刑法》对投标人之间的串通投标行为仅限定为“串通投标报价”。如果不能将投标人之间串通的事项解释为“串通投标报价”,那么便不能将该行为认定为串通投标罪。《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合计列举了属于或视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11种情形,串通投标报价属于其中情形之一,也即串通投标报价与串通其他事项为并列关系。本案中,对技术参数的串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解释为“串通投标报价”。文本的基本语义是《刑法》意义的基础,如果拘泥于字面含义,《刑法》变成僵死的教条,无法实现规制社会生活的目的;但如果脱离文本的基本语义,刑事法治就不可能存在。意图通过对串通“投标报价”作超越其基本语义的“扩大解释”来惩治串通技术参数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将来可通过修改《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将“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修改为“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既满足惩罚犯罪的现实需要,又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检察院)
 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
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