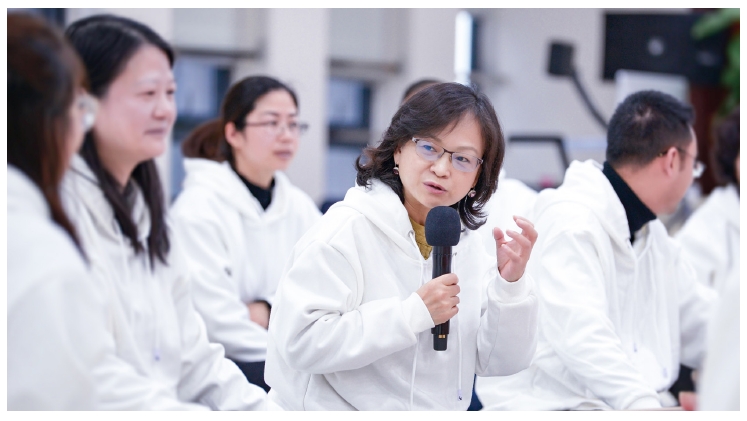《招标投标法》第46条第1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案例相关当事人对该条款的解释和适用存在差异。本文拟从该条款文本出发,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厘清本条所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以期给招标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实现缔约自由提供指引。
中标通知书的法律性质
法律规定的一般理解
《民法典》第473条已明确将招标公告界定为要约邀请,但对投标和发布中标通知书则未作规定。理论上一般认为,投标是“投标人根据招标人所公布的标准和条件向招标人发出以订立合同为目的的意思表示”,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包含了招标人和投标人双方主要的权利义务,因而投标符合要约的构成。发出中标通知书是对投标人投标行为的接受,且一经作出即对招标人和投标人双方产生约束力,符合承诺的构成。因此,发出中标通知书意味着招标人与中标人双方就标的履行达成了合同。
几种不同的司法实践
有学者对104个涉及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争议的案件进行了统计,发现持中标通知书为本约承诺说的判决占52.9%,持预约承诺说的判决占23.1%,持准法律行为说的判决占24%。[1]
持本约承诺说的案件援引的法律依据即为法律对要约和承诺的规定,如(2016)最高法民再123号判决书即直接援引《合同法》第13条。对于订立书面合同的要求,有判决认为,该规定属于倡导性法律规范,其目的是倡导、鼓励双方按照招标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合同的订立并非以书面合同形式,而是通过投标与中标通知书的方式,如(2019)沪02民终228号民事判决书;也有判决认为,招标过程中的各类文件均为书面形式,且有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符合书面形式要求,因此,中标通知书发出,合同关系即成立,如(2019)内01民终2854号民事判决书。
持预约承诺说的判决认为,中标通知书的发出仅使招标人与中标人产生预约合同,该合同与招标人和中标人就标的达成的书面合同属于预约与本约关系,招标人出具中标通知书的目的是为了之后订立合同,如(2016)黔民初295号民事判决书、(2021)新民终293号民事判决书。
持准法律行为说的判决则依据《合同法》第32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同时结合招标文件来认定,发布中标通知书的行为仅对双方产生签约义务,如双方未签约,则本约并不成立,拒绝签订合同的一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如(2019)甘01民终119号民事判决书。
“订立书面合同”应如何理解
以上三类判决,产生不同判决的原因在于对《招标投标法》第46条“订立书面合同”的要求和《合同法》第32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理解存在差别。2019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发布的《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第52条第2款规定“中标通知书到达中标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这就直接排除了准法律行为说,但有学者认为,这样仍不能得出发出中标通知书本约即成立的结论,此处的“违约”也可理解为违反预约。[2]
中标通知书的性质究竟是本约承诺还是预约承诺呢?本文认为,应是预约承诺。从第46条上下文来看,如中标通知书能够被认定为招标人的本约承诺,则完全没有必要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因为投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本身已是书面形式,且均有双方盖章确认。此处应对“书面形式”作缩小解释,将其理解为《民法典》第490条所规定的“合同书”,从而认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就标的签订的合同在双方均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时成立,中标通知书仅发生预约的效力,使双方产生签订本约的义务。
那么,能否将第46条解释为倡导性法律规范,从而得出不签订书面合同并不影响合同成立的结论呢?倡导性法律规范是对法律规范的一种学理分类,有学者对《合同法》中有关特定合同应采取书面形式的规定进行论述,认为这种规定是倡导性规范,倡导性规范仅具倡导性,只是提倡和诱导交易关系的当事人采取的行为模式。[3]但根据《招标投标法》第59条,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文件订立合同,可能导致罚款,这种要求显然不仅仅是倡导。如立法意图是招标投标买卖合同关系以要约承诺形式成立,则仅规定双方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文件履行合同的法律后果即可。因此,不能将“订立书面合同”的要求看作倡导性规定,而应理解为强制性规定,未签订书面合同,则合同关系不成立。

另外,从招标投标流程上看,很多招标文件中只包括标的、数量、质量要求、履行期限等必要条款,而不含合同范本,在完成招标后,招标人和中标人仍需就其他条款进行协商。在实际操作中,即使招标文件中已附有合同范本,双方仍有可能就具体条款进行协商和修改。“订立书面合同”应是一种强制性要求,招标投标合同并非以要约承诺的形式成立,而是以双方订立合同书的形式成立,中标通知书是招标人对预约的承诺而非对本约的承诺。
书面合同是否必须与招标、投标文件完全一致
《招标投标法》第46条的规定有两层含义:一是要订立书面合同,从而使双方就标的建立合同关系;二是书面合同的约定要与招标投标文件保持一致。但如上文所述,实际操作中,招标人与投标人在签订合同前,还会就具体条款进行协商并有可能变更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的条款。前文已论述关于订立书面合同的规定为强制性而非倡导性,那么书面合同条款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相一致的要求是否也为强制性的呢?这在司法实践中较为一致,尽管法院裁判理由可能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该条款属于强制性规范。[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以下简称《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了几种一方当事人以背离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为由请求确认无效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情形。但在强制性规范的类型划分上,法院裁判仍有分歧,下文将详述之。
结合《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57条来看,《招标投标法》第46条第1款包含了两个阶段的要求:在根据招标投标文件签订书面合同阶段,需要确保合同约定与招标投标文件一致;在上述合同成立后,双方就标的签订的其他协议仍需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一致。那么,第46条要求的“一致”指的是完全一致,还是主要条款一致呢?根据《实施条例》第57条第1款,合同标的、价款、质量、履行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也就是说,在招标完成后,双方不能就主要条款进行更改,但仍可就一些非主要条款进行协商。《征求意见稿》第53条也规定招标人可以和中标人进行合同谈判。但合同中,除了本条所列举的条款外,其他条款也可能对双方权利义务产生重要影响。以下根据司法实践中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变更诸如标的、价款、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条款的认定情况进行简述。
标的变更
在建设工程合同的签约和执行过程中,双方经常会对施工范围进行变更,此时判断是否构成对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的实质性背离,需要仔细甄别此种变更是根本性变更了施工项目,还是对原施工项目设计方案的修改,又或者是由于双方未在招标投标文件中列明施工所必须的配套设施或服务项目所导致的。如为后两类,则法院通常不会认为合同中对此部分的约定构成对招标投标文件的实质性背离。比如,在最高院2017年审理的一起再审案件中,中标人琼州建筑公司主张,小区道路、园林绿化等在招标文件中未体现,因而合同就该部分的约定无效,最高院认为,虽然招标投标文件中未体现上述内容,但其属于涉案职工住宅楼的配套工程,招标人与投标人签订的合同将配套工程列入施工范围并不违反《招标投标法》第46条和《实施条例》第57条〔参见(2017)最高法民再249号再审民事判决书〕。
价格变更
在建设工程合同中经常会出现中标价格与实际签约价格不同的情况。《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2条明确规定了向建设单位捐赠财物等几种变相降低工程价款可以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在实践中,不仅存在变相降低价款的情况,还有变更价格计算方式或招标人压低价款的情况。比如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约定固定总价,但合同约定实时结算〔参见(2018)川民初42号民事判决书〕;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约定综合单价计价方式,但合同中约定固定总价包干计价〔参见(2017)鄂民终1840号民事判决书〕;合同约定在投标价基础上让利一定比例〔参见(2020)鲁1621民初3009号民事判决书〕,或者中标人单方承诺让利,诸如此类的情形都会被法院认定为构成对招标投标文件或原合同的实质性背离,违反《招标投标法》第46条,因而无效〔参见(2017)京0115民初2464号民事判决书〕。
履行期限
尽管《实施条例》第57条明确将合同履行期限列举为合同主要条款之一,但在合同履行中,经常出现双方协商变更合同履行期限的情形。比如,建设工程的施工过程中,设计方案、施工范围等可能会发生变更,从而导致工期变更。法院在判断工期变更是否构成对招标投标文件实质性背离时会考虑变更的合理性,不合理地缩短工期有可能被认定为实质性背离〔参见(2019)豫民终1729号民事判决书〕,但多数工期变化是工期的推迟或延长,这些变化很难被认定为实质性背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的为数不多的其他类型的案件中也存在履行期限变化的情况。比如,一起租赁合同纠纷中,存在三份合同,招标签订的合同约定服务期两年,但在后两份合同中约定服务期十年,法院并未否认后两份合同的效力,法院认为《招标投标法》第46条的规定属于效力性禁则还是管理性禁则并不明确,且本案所涉标的并非法定必须招标的项目,延迟服务期并不违法,因此不认为履行期限的变更属于违背效力性禁则的情形〔参见(2021)浙06民终4809号民事判决书〕。
违约责任
如招标文件中含违约责任条款,中标通知书发布后或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修改违约责任条款,有可能构成对招标投标文件的实质性背离。比如,在一起案件中,招标文件约定迟交货违约责任为迟交货物价值的5%,且迟交货数量达20%的,招标人有权另选厂家,中标人须承担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和增加的费用;招标人要求中标人签订的合同中,上述条款修改为,迟交货违约金为每天支付迟交货物价值的5%,且迟交货超过7天,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中标人须承担招标人的一切损失。法院认为上述合同文本构成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背离。结合其他条款的变化,法院认为上述合同显著限制了中标人权利或加重了中标人义务,因此违反《招标投标法》确定的义务和《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参见(2016)豫71民终15号民事判决书〕。
从法院对实质性背离的认定来看,在判断条款变化是否构成实质性背离时,有些法院不仅会考察上述在《实施条例》中明确列举的条款变化,还会考虑其他条款的变化,比如付款比例、质保期等未列举的内容〔参见(2020)苏0703民初1609号民事判决书〕。根据这些判决理由,法院在认定是否违反《招标投标法》第46条第1款时,会进行两个层面的判断:
一是在事实层面上招标人和中标人的合同对招标投标文件的修改是否构成实质性背离。法律允许招标人和中标人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并对招标投标文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修改,第46条第1款所要求的“一致”并非完全一致,甚至有些情况下显著的不一致也未必被认定为实质性背离。在判断实质性背离时,法院会主要考虑条款变更是否对其他投标人产生不公〔参见(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70号民事判决书〕。多数被认定为存在实质性背离的案件都涉及多个条款的修改而不是仅一项约定的变化,法院会综合考虑这些条款的变化是否从总体上对其他投标人的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此外,有些案件中法院还考虑了条款修改是否显著加重了一方的义务或限制了一方的权利。
二是构成实质性背离是否导致相应条款的无效,双方是否应继续遵守招标投标文件中的约定。比如,在建设工程合同中,如当事人违反工程建设的强制性标准,任意压缩合理工期、降低工程质量标准,则会因违反强制性标准而无效,同时构成对招标投标文件的实质性背离〔参见(2019)豫民终1729号民事判决书〕。又如,针对中小企业,有关保证金的收取比例、收取方式、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等等还需要符合《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还需进一步考虑下一个问题,也就是《招标投标法》第46条第1款作为强制性规定的类型细分。
效力性禁止还是管理性禁止
部分案件认为第46条第1款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上文提到的效力性禁则),违反该规定会导致与招标投标文件实质性背离的条款无效,也有案件认为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即上文提到的管理性禁则),订立与招标投标文件实质性背离的条款并不当然导致约定无效。
从司法解释和最高院司法实践来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是相对的概念,二者的区别在于违反后果。违反前者将导致合同无效;而违反后者则不会,因为管理性强制规定意在“管理”而非否认合同内容本身。[5]根据《民法典》第153条,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取决于该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招标投标法》和《实施条例》都未明确规定招标人与投标人约定实质性背离招标投标文件的法律后果,导致实践中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
在最高院2015年的一起再审案件中,最高院认为,尽管招标人与中标人订立的合同与招标投标文件不同,但《招标投标法》第59条仅规定了责令改正和罚款的法律后果,并未规定合同无效,因此判断第46条第1款的要求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参见(2015)民申字第280号判决书〕。但根据2020年的《建设工程司法解释》,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中出现实质性背离招标投标文件的,如一方要求认定合同条款无效,法院应予支持。《建设工程司法解释》是裁判规则,而非对条款本身的释明或修改。在建设工程案件中,《招标投标法》第46条的规定应被理解为效力性强制规定,但在《建设工程司法解释》无法覆盖的其他招标投标案件中,《招标投标法》第46条第1款的性质仍可能存在争议。
招标人如何应对《招标投标法》第46条第1款的不确定性
从以上论述可知,《招标投标法》第46条第1款在招标实践中可能存在两层不确定性,一是未签订书面协议可能导致违反预约、违反本约或缔约过失责任,这三类责任对于招标人和中标人来说可能是不同的;二是中标人与招标人签订的合同条款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与招标投标文件不同,并使条款的效力在发生争议时为法院认可。
就第一点来说,为避免不利的法律后果,招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与中标人订立书面合同。上文已论述过订立书面合同的要求为强制性规定,但该条款规定的“30天内”的时限要求却无违反后果,应属于倡导性规定。如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超过中标通知书发布后30天,也并不会导致合同无效或使一方受到行政处罚。中标人此时应注意招标文件对此是否有相关约定,因为违反招标文件的约定有可能导致违约责任。同时,根据《实施条例》第74条,中标人在签约时不能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比如附加合同的生效要件。
就第二点来说,在中标通知书发布后,双方对合同条款进行协商的情况非常常见,此种协商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地位,也取决于招标文件对合同条款是否有较为明确的约定。对招标人来说,为尽快完成签约,可以在招标文件中附上合同范本。但范本中应避免存在明显加重中标人义务或减轻招标人责任的条款。如中标人要求修改合同条款而迟迟不肯签订合同,招标人也可据此告知其可能的违约责任,以督促其尽快履约。双方在协商时,应避免对招标投标文件中已经明确的标的、数量、质量标准、技术参数等进行变更;对履约时间、付款方式、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修改时应避免减轻中标人义务对其他投标人造成不公,还应避免过度加重中标人义务使合同条款存在效力不被法院认可的风险。
注释:
[1]参见何红锋、郭光坤,《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的实证研究》,载于《招标采购管理》,2019年第7期(总第83期),第34页。
[2]参见陈川生、李显冬、沈玥,《关于中标通知书法律思考》,载于《中国招标》2021年第3期,第5页。
[3]参见王轶,《论倡导性规范——以合同法为背景的分析》,载于《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第1卷,第70页、第73页。
[4]参见邬洪明,《浅议〈招标投标法〉“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条款的适用》,载于《招标采购管理》,2019年第5期,第58页。
[5]参见朱庆育,《〈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评注》,载于《法学家》2016年第3期,第158页。
 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
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商